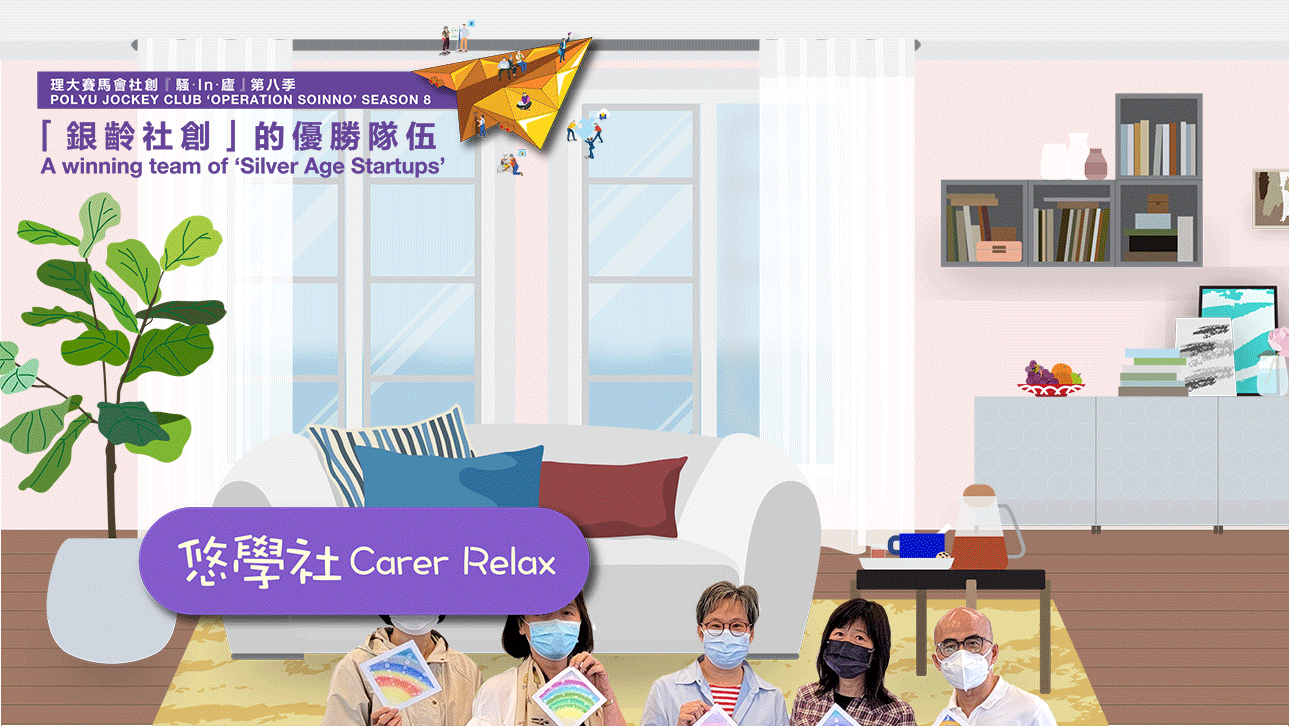這天,他們五人聚在一起,希望完成一幅和諧粉彩畫,回顧這半年創業的困惑和成果,談起這幾個月的變化。
Lydia、淑儀是悠學社的導師,Lydia擁有和諧粉彩和伸展運動的導師資格。而淑儀就是皮革手工和押花藝術導師。Maria 就負責對外聯絡,Shirley 自認不太懂教班,但就懂得行政管理,是悠學社的書記,阿Kent 則自己什麼都不懂,負責悠學社的宣傳設計。
回想團隊起初的理念,是想降低藝術活動的參與價格,使更多人可以受惠於藝術的紓緩精神壓力的好處,但由於這個範疇太廣泛,社創的導師引導他們想得更深入一點,就是想要針對的服務對象是誰,如何才可以增加項目的社會影響力呢?
在討論服務對象時,組員都有不同的意見。有人提出可以服務照顧者,但作為照顧者的Maria 和Lydia 一開始表現就有些抗拒。Maria 解釋說:「我一開始其實不想再做照顧者,因為我和Lydia已經係照顧者。我一直照顧我父母,雖然他們已經去了天家,現在我仍是照顧者。恍似,照顧者就是我的天職。」對Maria 和Lydia來講,照顧者就好像是一個擺脫不了的身份和責任,想起已是一種無形的壓力,但無可否認地,他們都認為社會應為照顧者提供更多的支援。
現時政府沒有就照顧者作專門的統計,但由零散的數據中反映社會上有為數不少的照顧者。如果把殘疾人士、長期病患者、長者及有特殊需要學生的人數加起來,在他們背後應隱藏著數以十萬計的照顧者,默默地為社會貢獻。
另一位隊員Shirley 都十分同情照顧者的情況,「我雖然不是照顧者,但我媽媽是一位照顧者,要照顧我受了傷的爸爸,這麼多年來,我見證了我媽媽承受著很大的的壓力。例如,她不敢和其他人講自己的狀況,我作為她的兒女也不敢多問,都幫不到手。照顧者真係無援。同時,他們的兒女或者整個家庭其實都受著很大壓力。所以我很想做一些事情來幫助照顧者,同時幫助他們的兒女。」
Maria 亦分享在社創活動的過程中,接觸到不同照顧者的經歷。「DISI 的工作坊推動我們去深化問題,這對於悠學社的定位很有幫助。比如,其中一份功課是要我們去訪問服務對象,其中我訪問到兩位患癌症老夫妻,他們各有自己的病痛,但都要照顧對方。令我想到,受照顧者和照顧者可能是同等地位,只是可能一個比另一個強壯了少少。這令我想起了當年日夜照顧母親的時候,如果當時可以有些遊戲治療師,帶給我們短時間的開心,也很滿足。我們做照顧者的,也希望有個放空的時間,如果可以加一點學習的原素,就會有更大的幫助。因為經歷過,更知當中的困難及孤單無援,很想將我過去的經驗同人分享,藉住一些紓緩的活動,苦中作樂,與各位同路人走下去。」